中国文坛不乏编辑兼大作家者。比如,叶圣陶先生是知名的三大家,即编辑家、作家、教育家。他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发现并培养了丁玲、巴金等著名作家。后来叶圣陶为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特辟了《青年论坛》和《青年文艺》,又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同时他又是
文坛上的一位多面手,创作的长篇小说《倪焕之》、童话集《稻草人》、《多收了三五斗》等影响深远。郁达夫曾主编《创造季刊》、《洪水》、《大众文艺》,他的作品《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有强烈反旧礼教意识;茅盾于1921年接编改革《小说月报》,对新文学运动产生巨大影响,而他的《子夜》、《林家铺子》等,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朱自清和俞平伯等创办《诗》月刊,胡风办《七月》等杂志,丁玲主编过《北斗》杂志。当下的文坛,也活跃着一批编辑家或出版家,他们的职业是刊物主编或副主编,但同时又创作出很多有分量的优秀作品。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有利还是有弊?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对他们展开调查。
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恰恰是职业为作家提供了稳定的写作环境。比如阿来,如果没有《科幻世界》的职业,很难说用十年功夫去思考、构思长篇《空山》。而且因为他们从事编辑工作或与文学相关的工作,给作家在这个圈子里提供了很多方便;职业同时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果纯粹的写作,可能会有商业上的考虑,与现在的写作方向不可能一致。因为写作不是谋生手段,写作上便相对自由。如果关系处理得好,职业对写作应该有利,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体验。比如铁凝,她身为河北省作协主席,日常性工作很多,她推掉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有些她也不推掉,介入工作可以为她提供新的写作经验。这个事情很难严格定义。也有一种情况,写长篇的作家可能会感到工作对他的约束。
赵长天:《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 比任何一部作品都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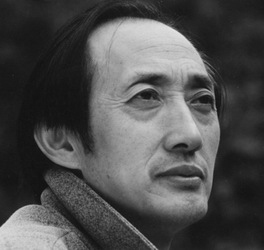
当专业作家一直是赵长天的梦想。30多年的写作经历中,很多时候他别无选择,在与文学若离又若即的工作环境中,他的梦想一直未曾实现。
70年代初,赵长天在空军部队报道组搞新闻,正好碰到林彪事件,上级命令空军人员不得离开驻地。不能出去跑新闻,赵长天便待在机关里写了篇散文,投给《四川日报》,很快发表了。后来部队组建文工团,需要创作人员,在报纸上看到赵长天的文章,便把他调到文工团,进入成都空军创作组。当时的环境没法搞文学创作,1976年赵长天复员后,选择了工厂。文革后,《上海文艺》(1979年更名为《上海文学》)复刊了,赵长天在上面发表了《快板连长》,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影响很大。后来,他陆续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些作品。1982年,赵长天调任上海航天局,任宣传处长。
1985年,上海市作协文联分家,筹建作协,征求赵长天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到作协。一直想当专业作家的赵长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没想到去作协后,主席团开会成立书记处,任命赵长天为常务书记。本来以为可以搞专业创作,没想到常务书记这一秘书长的角色,带给他的是更为琐碎的行政事务。
1995年,秘书长的职务还没辞,赵长天又被任命兼职《萌芽》主编。当时的《萌芽》发行量只有1万份。赵长天先去了做市场调查,发现定位为青年文学刊物的《萌芽》,读者主要是中年人,他们是《萌芽》的铁杆读者。中学生、大学生中,没有人知道《萌芽》。青年文学刊物,最后弄成中年文学刊物,也许将来会变成老年文学刊物。所以赵长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新定位。80年代,《萌芽》的口号“青年作家的摇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这毕竟是小众的定位,何况到了90年代,期刊进入市场竞争,定位必须在大众。赵长天决定把定位修整为“提高文学修养”。对于青年人来讲,提高修养是必需的,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作家。定位的转变,冒着相当风险。当时有很多不同意见,一向走高雅路线的《萌芽》介入大众商业的东西,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可?赵长天就一个目标:必须让年轻人爱读。他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尝试多种方式把读者吸引到杂志上,一年多的时间,《萌芽》发行量增加到两万多份。这时,赵长天又发现一个问题。《萌芽》不仅是读者老化,作者也老化,没法吸引年轻读者。最好是搞作文比赛,按《萌芽》的标准找一些好文章,好作者。《萌芽》缺乏号召力,那就和大学联手。好在大学教授和赵长天的看法比较一致,希望多渠道地选拔到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生。
“新概念作文大赛”就这样开始了。目前为止,大赛进行了七届,韩寒、张悦然、郭敬明、小饭……当前大部分活跃的年轻作家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或是从《萌芽》冒出来的。
现在《萌芽》的发行量达到50多万份,在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萌芽》把年轻人重新吸引到文学中间来,这是赵长天很感到安慰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收到众多的小读者来信,他们说,写作原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以这么有意思。赵长天说:“我们喜欢文学也是从中学开始的。中学生其实对文学非常热爱,天然有种表达、诉说的欲望,对文学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只是文学的阶梯,让大部分年轻人接近文学、热爱文学。”
但是,一直没有多的创作时间,这使赵长天处于很不甘心的状态。在作协任常务书记,他常给人家放创作假,自己却从没有过创作假。创作了5部长篇,几十个中篇,都是利用晚上或者星期天的时间。他只请过一次20天的假,写了一个长篇《天命》。赵长天说:“我自己觉得写作是有问题的,很难投入地创作。特别是写长篇,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但是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如果研究我的小说,会发现我的创作始终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缺乏该展开的部分,比较平,冲击力不大,爆发不出来。我自己很明白这个问题。但我进入不了,老被打断。”1995年,他的中篇《不是忏悔》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长中篇小说奖。在颁奖大会上,赵长天说:“得这个奖我很高兴,因为有机会可以证明我是可以写作,不是只能做秘书长的。”他非常希望能有机会证明自己能写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样的机会从来没有过。
过去,赵长天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行政工作,从事专业写作。现在虽然也没有办法拿出整块时间创作,他却不会放弃编辑工作。他认为编辑这个职业,不一定比写作没有价值。《萌芽》渐渐步入良性循环,在市场竞争中,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赵长天每天都要到《萌芽》杂志,他没有办法丢掉这份牵扯着所有编辑利益的《萌芽》。对他来讲,从行政干部到作协,再到《萌芽》,他的职业和创作始终有矛盾,而且无法解决。但是,他说:“萌芽是我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比任何一部作品都重要。”
赵长天有个创作计划,长篇开了个头,却进入不了写作的氛围。他认为中国没有很到位的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他很想写一部知识分子的长篇。“如果写出一部很一般的作品,还不如不写。要写,一定是别人没有写过或者没有达到水准的作品。当编辑容易眼高手低。编辑过程中会不断考虑、分析人家作品,不断地会对作者提出要求,老觉得不满意,临到自己写的时候,标准高了,不知道自己能否达到表达的水准。我不敢自信地说,一定写出非常优秀的小说,我可能写得比过去好一点。”
阿来:我最终要回到写作上去
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后,有4年的时间,阿来到处寻找出版机构,然而没有人肯接受这部作品。原因有二,一是少数民族题材敏感,二是市场化的环境下,这类纯文学的小说不卖钱。阿来感到很奇怪,他发现中国的出版界出现一种病态,他们假想读者在市场化的口号下庸俗化,认为要满足读者需要,只能是往俗里做。读者有分众,他们的需求是有高低的。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真正做到市场化。有一点选题、一些炒作,并不算完全市场化,他们没有做认真的市场调查。一位出版社的社长是阿来多年的朋友,他对阿来说,你的书我一定出,亏钱也出。阿来毫不犹豫地拿回了自己的书。他说:“我希望你赚钱,也希望我也赚钱。你没有认识作品的价值,不只文学的、美学的,还有市场的价值。”
《尘埃落定》不能顺利出版,阿来反思了很多:“我在想,中国的出版出了什么问题?不俗到死不罢休,不暴利到死不罢休。我希望有机会尝试一下,可不可以不言情,不武打,不侦探,不香艳地来做文学。”
1997年,《科幻世界》面向社会招聘人才,阿来离开阿坝文化局,来到杂志社,并推却了《科幻世界》给予的领导职务。从一名普通编辑做起,很快,阿来以自己的工作、见识和理念,赢得大家的信任。阿来坦率地说,到《科幻世界》之前,自己不知道科幻是什么,但是如果对一件事情发生兴趣,会很快地投入其中学习。半年后,阿来做了策划总监,之后又任《科幻世界》总编辑,《科幻世界》又派生出《科幻世界・译文版》,《科画刊》、《奇幻世界》,从十几万册的发行量发展到四十多万。
阿来认为,中国是科学意识很差的民族,中国青少年第一需要想像力。我们的文学有责任培养这个能力。阿来曾组织过读者问卷,回收的3万份问卷中,70%的读者都是高中生至大二的学生。这使他感到安慰与自豪:“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是少年中不知不觉中埋伏下来的东西,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这些阅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现在的阿来,依然每天和同事们一起,甚至提前十分钟打卡坐班,他没有因为创立了一个杂志的优秀品牌而居功自傲,也没有因为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需要创作而迟到早退。《科幻世界》越做越大,也许将来会发展成集团,但那只是量的积累,最初创业的艰难和动力没有了。也因此,阿来想离开《科幻世界》。出版对阿来,是一段宝贵的经历。他在这里体验到创业的艰难,与朝夕相处的同事共同打造了一个《科幻世界》的神话。但是,他的根本性的追求,不是出版人,他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写作上去。他说:“《科幻世界》给了我深刻的体验和自信,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刊物占用我50%的精力,我也会考虑不离开。将来退出《科幻世界》,我将会集中两三年时间写作。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需要每天写作的人,只要把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就行。我肯定会远远离开出版这个行当,去做完全不懂的事情。这是个学习的过程。”
阿来认为,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对社会是不正常的,是虚假的,这不是作家的方式。但是你写作外有一个职业,使你跟社会有了接触的点,没有人把你看成一个作家,你就是出版商,对一个印刷厂的老板来说,就是给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对政府部门,就是为他们提供可以服务的对象……这样你对生活才有真切的体验,而不是深入。在《科幻世界》的几年间,阿来有两点最重要的收获:第一,这几年,《科幻世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感同身受。将来也许不会直接写这种东西,但人生的很多经验是相通的,他对人性的复杂性认识的更深刻,改革不是电视剧写的那么简单。二,对自己更加自信,一个男人需要成功,如果两三个方向都成功,很能提升一个人的自信。我的自信不是偶然的成功,而是带着一些理念。写《尘埃落定》,大家不那么写我偏那么写;做《科幻世界》,别人认为办不下去,我偏那么办。我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找到刊物和读者牢固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我将来做别的事情,或者写作,将坚持我个人的探索。至少我的读者是需要这些。
这几年,不论阿来的个人写作还是杂志运行,都证明了阿来的想法―――文化不需要做得那么低俗不堪,公众中有相当健康的、高雅的、正当的需求,而文学对这个需求满足是不够。这个成功,给我们的出版界和文化界应该带来一些启示。
何建明:大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应该是文学家
今年“五一”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何建明是全国惟一一位以作家身份进入全国“劳模”行列的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杂志执行副总编的何建明,曾创作出《落泪是金》、《根本利益》、《中国高考报告》和《北京保卫战》等享誉全国的作品。这位以关注弱势群体、歌颂北京“抗非”战斗和反映重点工程建设等重大题材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在近几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一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而且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表扬。到《中国作家》的十年,是何建明创作的高峰期。他的几部有分量的作品都是这十年完成的,其间,他得过两届鲁迅文学,两个徐迟报告文学奖,五个全国年度报告文学奖,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优秀报告文学》选编中,都有他的作品。好多人以为他是专业创作,其实何建明70%的精力放在编辑工作上,写作时间很少。
在《中国作家》,何建明主要担任广告、创收、发行等方面的工作,行政事务繁多。何建明认为,文学刊物有导向作用,一个刊物要有影响,必须发大作品,有冲击力、震憾力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中国作家》渐渐形成以长篇为主的风格,有时一本杂志只发一部作品,《马家军调查》,《落泪是金》等作品发表后发行量达到十几万册。看到刊物和作品有反响,何建明发自内心地高兴。《落泪是金》发表后,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写作对象的命运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本利益》发表后,很多百姓扛着铺盖到北京找何建明打官司,这对他触动很大,更感觉到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过去大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都是大作家,现在这种情况弱化了很多。一般来说,好多编辑当久了很少写东西。何建明倒觉得,文学刊物的大编辑,应该成为文学界的作者或大作家,这样才能把握大刊物的质量和导向。如果编辑不是作家,对作品感觉有差异,对文学和刊物发展也有影响。怎么才能处理好编辑和写作的关系非常重要,二者既矛盾又统一。高明的主编重要任务是要考虑报纸、刊物发展的战略,不是大家,怎么能使刊物引领文学的潮流?他认为,对于创作来说,做编辑对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看稿多了,自然有感觉,对创作有些触动,对一些题材以及对创作技巧、结构的把握会有所提高,但这也因人而异。对何建明的创作来说,这种帮助很少,他喜欢独立写作。何建明说,当编辑又写作对自己来说是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他写长篇比较多,别人下班了他在写,别人放假了他还在写。出去采访也是跟杂志的工作结合起来。出去一周,实际上是完成两周的工作量。最近这几年,他的作品都是利用长假完成的,他已经连续四个“5・1”长假没有休息过了,利用这一长假,2000年完成《中国高考报告》,2002年完成《根本利益》,2003年完成《北京保卫战》,2004年完成《永远的红树林》,今年“5・1”,他又跑到华西去采访。
如果有机会专职写作,何建明说自己会考虑放弃编辑的职业。“我更倾向当作家。刊物的这个担子太重,太累。当副主编,承担是的整个杂志的工作,创作纯粹是独立的行为,需要全身心投入创作。我现在有70%的时间要投入到杂志中去,而且总被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情绪。”接下来两三年的时间,何建明已全部排满,他每天要写5000字,才能完成写作任务。这样繁重的写作任务,他却一直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这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写作立场和观念。他总不太满意当下的一些作家缺少时代的主流意识,并不是非写主旋律作品,只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完成大题材,而这方面恰恰是缺少的。他说,很多作家跟主流生活脱离,有些边缘化,生活处在贵族状态,很少接触现实生活,靠网络或媒体的信息了解、感受生活,这和实际生活的差异很大,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我们应该有激情去感受生活完成主流生活的主流作品,表现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行。
金娜:办刊物和写作,两头对我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1998年大学毕业后,金娜进入《电影故事》,当了一名记者,多年的记者生涯使她受益匪浅。她说:“做记者非常好的一点是,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和通道,了解平时人们了解不到的文艺圈中泰斗级人物,像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有成功的不同因素,迅速进入他们思想的层面,对年轻人的成长很有帮助。他们教给我一些道理,也许只是阐述他们的观念,但是对我很有启发。拍电影常常选择冷僻的地方,我的工作要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如果你擅于感悟,会发现行走本身带来很多智慧。我在行走过程中发现新的东西,视野开阔了。此外,当记者的人,善于察言观色,这不是贬意词,证明有你细腻的灵魂和感觉的触角。长期以来和著名的大师聊天,真是需要察言观色,因此看人看事情,会比一般人敏感。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必备的。”
回顾那段快乐、紧张而充实的生活,金娜觉得很欣慰。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把这些事都做了,而当你打算写的时候会发现,你是为工作,实际是为自己的写作积累一些经验。如果有可能,应该尽量追求自由的生活,尽可能去尝试各种不可能。
金娜很快成为《电影故事》的主力记者,撰写了大量文字,有时一期写了三万字,几乎半本杂志是由她主笔。写字是枯燥的,如果没有耐心和积累,会坚持不下来,但因为长期不断地在写,文字完全没有障碍地在笔尖或者键盘上流动,这种流畅的感觉令她心驰神往。2004年10月,金娜上任《电影故事》主编,做一本有着53年历史的专业电影杂志的主编,面对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当时金娜还不足30岁,是文广系统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上任后,她改组了《电影故事》的经营管理结构,联手上影电通改组杂志,吸纳资本,将64页的月刊改版为128页的半月刊;之后重建内容、发行、广告团队,并联手电影频道举办“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上海市大学生电影知识大赛”等大型活动,参与制作几档电影栏目,目前正在筹备全国范围的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她以自己的学识和魄力赢得了同事的信任和尊重。
金娜从小非常热爱写作。在她的内心,一直把写作放在神圣的位置。以这种心态写作,金娜的《上海浮世恋》不会令人失望,三个月不到,发行量1.5万册。同事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无法想象金娜是什么时候写作。她笑着解释:“我的生活极其简单,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白天做一个职业经理人,抓选题,谈项目,开拓各种合作渠道,为了杂志社十几口人的美好生活奔忙。会发现遇见的每一个人起码有一点、或者一句话入得了画,进得了文学。晚上做一个文字的苦行僧,打字直到身心俱疲,写到枯竭,再也写不下去,歇笔,睡觉。只要有感觉就写。我相信一句话,当你坚定不移地写下第一个字,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办刊物和写作,金娜都放不下。放不下就说明两头对自己都有致命的吸引力。她说:“好在我总是从好的方面想遇到的困难,就像我总是从坏的方面想可能碰到的机遇。我自省,是这个世界上很少的拥有多重角色的人,我始终对自己,也对我们的员工说,学会‘额外付出’,如果一个人只做交待给你的事情,那你永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她想,也许有一天会有放弃编辑,专职从事写作这样的幸运。但今天,她依旧在多重角色间承受巨大的压力,也获得巨大的快乐。除非哪一天,她觉得那些繁忙的日常事务让自己非常不快乐,她会放弃。“到现在为止,尽管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过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有时候会对我表示同情,但他们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偷着乐呢。逛街、泡吧,尽管我的小说中会出现这种场面,其实生活中我几乎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相反,每当我开始写作,而不是去逛街的时候,我都被一种巨大的快乐所笼罩,认为自己在做上帝希望你做的事情。为人类文化奉献着,我始终觉得无私奉献是一种美德,应该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尽量献给一种非凡的事业,哪怕这能力微不足道,但我坚信,每个人只要有心奉献,就别在乎能力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