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弗吉尼娅・伍尔夫
中:向弗吉尼娅・伍尔夫致敬的影片《时时刻刻》 右:妮可・基德曼在《时时刻刻》中饰演的伍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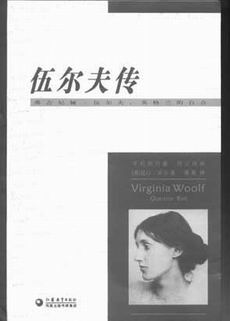
1941年3月28日,一个晴朗、明净、寒冷的日子,弗吉尼娅・伍尔夫给她生命中最爱的两个人――伦纳德和瓦奈萨――写告别信,然后,她从熟悉的生活环境逃逸了,带着手杖,不是到灯塔去,而是穿越浸水草甸来到河边,她放下手杖,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外套的口袋,走向冰冷的河水,走向死亡……
读昆汀・贝尔的《伍尔夫传》,我是从结尾开始读的。这也是一个隐喻,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伍尔夫解脱了贯穿她一生的种种痛苦,摆脱了像梦魇般的抑郁症,走向永恒。她选择了水,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溺水而死的奥菲利娅。不过伍尔夫选择自杀时,是清醒的。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认为,此前她尝试过一次溺水,她再次走到河边时,已经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
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影片把伍尔夫自杀放在一个金色的黄昏,试图营造一种令人感伤的氛围,事实上,那天是正午,阳光灿烂,但弗吉尼娅无法摆脱内心的阴影。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娅・伍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门22号。其父是文学家兼评论家。弗吉尼娅自幼受其父影响,她的许多作品都与早年的经历有关。复杂的家庭背景,这个9口之家、两群年龄与性格不合的子女经常发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伍尔夫同母异父的两位兄长对她的伤害给她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她的经历让我想起英国文学中一个经典形象――苔丝。
在某种程度上说,弗吉尼娅是上帝的弃儿,母亲、父亲相继病逝,是她难以承受的打击。她的小说《达洛威夫人》中即充满了对病态幻觉的真实生动的描绘,可以说是她的精神写照。弗吉尼娅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她如含羞草一般敏感,又如玻璃般的易碎,她是优雅的,又是神经质的,一生都在优雅和疯癫之间游走。有人这样描述弗吉尼娅,准确地把握住她的精神气质:“她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
弗吉尼娅和伦纳德(一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结合,使她的婚姻生活与文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其夫的帮助与支持,她或许成不了伟大的作家之一。读《伍尔夫传》时,我留意弗吉尼娅和当时作家、艺术家的交往。伦纳德创建的霍加斯出版社差点儿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是因弗吉尼娅看不惯《尤利西斯》的“粗俗”才与其失之交臂。
昆汀・贝尔的《伍尔夫传》重点揭示伍尔夫的精神状态,描述她的创作过程。但写到弗吉尼娅少女时期遭受的精神创伤――其同母异父的兄长对她多次进行性骚扰――小心翼翼,偏重于年少时经受的性骚扰对弗吉尼娅的影响,昆汀・贝尔认为,弗吉尼娅的神经错乱和自杀前的幻听,和这无法愈合的伤口有关。事实上,弗吉尼娅成人后非常厌恶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对于同性的依恋甚至一度成为她感情世界里的重心。诚然对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复杂多变的情感关系,并不能以常人的眼光等闲看待,即便如此,弗吉尼娅的情感状态依然被认为是出格的。她不可救药地依恋着姐姐瓦奈萨,甚至采用一种最为出人意料的极端方式――和姐夫克莱夫调情,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感情替身或者说傀儡。弗吉尼娅和瓦奈萨,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始终是被关注的焦点,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除了她们的艺术才华,还有她们的生活隐私。
弗吉尼娅・伍尔夫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不过,她每完成一部作品常会出现病兆,性格多变的她经常在脸上折射出内心的痛苦。唯一值得庆幸的只是她的每一场发病,都有丈夫伦纳德在身边无微不至的照料,这无疑带给弗吉尼娅极大的鼓励和感动,“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我早开枪自杀了。”当疯癫和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重复来袭,最终不堪忍受时,她还是想到了自杀,在给伦纳德的遗言中她这样写到:“我不能再毁掉你的生活了。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一向更开心了。”
《伍尔夫传》的作者昆汀・贝尔是伍尔夫幸存下来的唯一的外甥,自幼生活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深受自由主义意识的影响,同时,他本人也是英国著名的艺术家。本书问世后好评如潮,曾获英国詹姆斯・泰特・布莱克传记文学奖。
读罢《伍尔夫传》,凝视着封面上弗吉尼娅,美丽的容颜、不凡的才情和气质,如一枝圣洁的百合,在诗意的空间恬淡而又孤寂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