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纽约城市大剧院上演的《卡门》中烟厂女工合唱的场景
在西方文化中,吸烟一直是矛盾的结合体。作为兴奋剂和弛缓剂,吸烟既有医学功效也能置人于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展示吸烟矛盾性的歌剧登上了欧洲的舞台。历史证明,歌剧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反之也会影响社会。例如,历来香烟广告表现的西方人耳熟能详的友谊和兄弟情谊也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和雅克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等。歌剧还采用了电影用吸烟塑造反叛形象的做法,吉亚卡摩普契尼在歌剧《西部姑娘》中塑造的杰克兰斯成为之后亨弗莱鲍嘉、詹姆斯迪恩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扮演的诸多电影人物的模板。
鉴于歌剧长期以来一直迷恋于生和死、激情与暴力的主题,因此吸烟主题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歌剧保留并充分挖掘了吸烟与声色欢愉和色情的联系,并加入另一种令人忧虑的东西:男人的忌妒和暴力。这两种主题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的歌剧中,足以说明它们确实能让表演更加生动和深刻。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最初最温和的祈祷,最后都会暗藏杀机。例如,在沃尔夫―费拉里的《苏珊娜的秘密》中,我们见识了一个对香烟的芬芳怀着纯真无瑕的赞美之情的“叛逆”女子。被苏珊娜爱称为“我那带着香气的小毛病”的香烟,却是她向新婚丈夫极力隐瞒的东西,因为她知道她这个阶层的女子吸烟是多么的失态。妓女们可以叼着香烟来招客,但人们绝不会相信像她这样的资产阶级妇女也会有这样的嗜好,因为吸烟只是男人的事情。因此,当她的丈夫闻到她身上的香烟味便误以为她早有情人。在他以暴力宣泄了忌妒和暴力之后,最终真相大白。尽管他的过激反应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暴力像奥赛罗的妒忌一样具有潜在的悲剧性。故事的最后,妒忌的丈夫认为妻子不应该放弃她的爱好,他要和她一起吸烟。然后,她为他点上烟,俩人一起唱着:真正的爱人,一刻不停地吸烟。然后他们又夸张地用一支蜡烛为各自点上一支烟,慢慢走向新房――被世俗认可的资产阶级享受新婚的地方。这部喜剧承认了香烟与享乐和色情的多种联系,同时也温和幽默地暗示了香烟对中产阶级秩序的威胁。
与香烟和吸烟有关的歌剧中最有名的要算乔治比才的《卡门》(1875),一个由男人的妒忌和女人的独立引发的悲剧。整个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但文化背景却是法国的。该剧改编自梅里美于1845年创作的流行中篇小说,该小说根据一个法国人在西班牙的亲身经历写成。《卡门》在巴黎歌剧院的首次公演由于打破了很多地方性舞台禁忌而惨遭失败,其中之一便是一群一边吸烟一边扭打在一起的女子的合唱,这些女子是故事中塞维利亚的一个著名卷烟厂(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卷烟厂)的女工。在卷烟厂门前,歌剧拉开了序幕。19世纪时,这个位于塞维利亚郊区的厂房把守森严,因为里面成百上千的女工正在用纤细的手指卷着烟卷,酷暑难当时,一些人常常半裸着身体。一般男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确实有一些人为了得到通行证而惹了麻烦。事实上,卷烟厂很快成了许多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男性访客的必经之地。不久,随着戈蒂叶、比埃尔路易士、莫里斯巴莱斯等作家的造访,卷烟厂和里面的女工渐渐成为法国色情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作家对这些裸女的描述既让人向往又令人望而生畏。
法国的剧作家把他们的“卡门”安置在塞维利亚卷烟厂,并让她的工友们齐声歌颂吸烟和爱情,这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不同于偷偷摸摸吸烟的苏珊娜和她丈夫的资产阶级风格,认为持续的吸烟便是真爱,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工们认为爱情的短暂就如同吸烟的片刻,她们同样也强调了吸烟的乐趣,这正是吸烟超越社会阶层的意义所在。剧作家就这样把卡门放在吸烟的背景下,自己这个风骚撩人的女人是这样赞美香烟的:它变化莫测,如吉卜赛人般叛逆。这也是对她最恰当的描述。在许多版本中,卡门均以叼着香烟的形象出场。从卷烟厂门外吸烟的护卫及其他男人嘴里以及他们的歌唱中,我们知道卡门性感迷人。当因与工友打架而被捕时,她表现得激情澎湃而叛逆;当说服逮捕的士兵唐霍塞释放她时,她的独立和决心彰显无遗。
卡门和霍塞的爱情家喻户晓,爱上了斗牛士的吉卜赛女郎最终被妒忌的前情人杀害。这个结局也撼动了另一个禁忌:卡门是第一个死在巴黎歌剧院的女主角。从观众的反应来看,显然这一越界加上卡门在诸多方面的冒犯让巴黎观众忍无可忍。巴黎歌剧院的总监卡米尔都洛克勒这样说:“巴黎歌剧院这样属于家庭、举行结婚仪式的地方怎么能出现吸烟的吉卜赛女郎?”对首次公演的评论一边倒地谴责被谋杀的女主角,而同情被她勾引的那个可怜无辜的男人。为什么19世纪晚期的巴黎观众会站在唐霍塞一边,认为卡门的死是她自己咎由自取,而不是他冲动、妒忌和欲望的后果?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当时法国人是如何看待西班牙妇女和吉卜赛人的。
雨果在于1829年创作的《东方诗集》中,从欧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将西班牙置于非洲和东方之间,为法国将“欧洲的这部分”东方化埋下了伏笔。西班牙妇女,尤其是安达卢西亚妇女以性感著称。但是在舞台和文学作品中,人们才对吉卜赛女郎有了完全的认识。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一样,是法国人可以在自家地盘上天天见到的外国人,是欧洲人眼中的“异类”。人们用动物形象来描述梅里美笔下的卡门的野性美、凶狠和异域道德观。她被表现得风骚撩人,同时也狡猾恶毒。为迎合巴黎观众的胃口,舞台上的卡门被“驯服”了许多,但她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吉卜赛女郎:性感、淫荡,既是万迷人又是危险分子。她是一个吉卜赛人的事实又让人们联想到游牧民族摆脱世俗约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历史上,罗马民族的语言、历史和道德准则都自成体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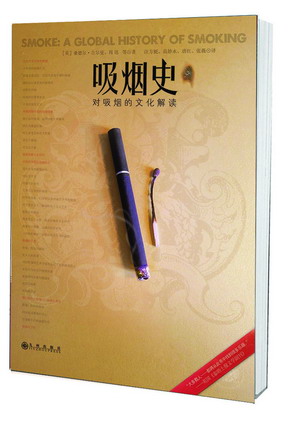 可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人却被迫害,被人们看作是凶险、迷信、令人恐惧的外国人。这种负面的印象从头到尾地出现在梅里美的小说中,尤其是在1847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不讲道德的吉卜赛女人。
可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人却被迫害,被人们看作是凶险、迷信、令人恐惧的外国人。这种负面的印象从头到尾地出现在梅里美的小说中,尤其是在1847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在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不讲道德的吉卜赛女人。
卡门的性别和社会身份中的独立性,使她成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如同所有的戏剧形式一样,歌剧必须把观众考虑在内。在19世纪,剧作家可以借助吸烟的两面性来复杂化、深化舞台表演的冲突。然而在吸烟的文化和医学意义都发生改变的今天,这种做法便显得问题百出。在现代版的《卡门》中,女主角和她的工友们仍然在吸烟,这或许是因为相对于吸烟与声色欢愉的联系,吸烟还象征着男性的暴力和妒忌。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歌剧的表现形式随文化背景、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然而,或许仍有一些连续性是永远挖掘不尽的。
本文摘自《吸烟史――对香烟的文化解读》,[英]桑德尔吉尔曼、周迅等著,江方挺、高妙永、唐红、张薇译,九州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