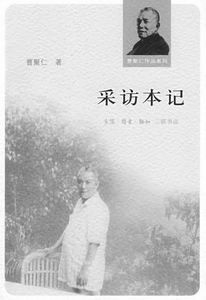
三联版曹聚仁著《采访本记》
曹聚仁先生是现代中国的著名记者、学人和作家,一生著述颇丰。爱好历史的他,连编带写,光是各种大部头的书籍或许就不下几十本。如果称之为“著
在后记部分第206页,曹聚仁谈到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自己曾收集了一些战史材料。但是,千辛万苦得来的地图随后却毁于“金华之役”,而好不容易弄到的战斗详报和作战日记,起先寄存于上海怡和洋行,但最终“也以日军进占租界,毁于‘一・二八’的早晨”。按此处的“一・二八”,应为“一二・八”之误。从上下文看,前面确实提到了“一・二八”事变,而且曹氏也确实从俘获的日军文件中收集到《“一・二八”战役纪念册》,但是所谓因日军进占租界而使得相关史料“毁于‘一・二八’的早晨”,则显然有误。按“一・二八”事变爆发于1932年,而且其时日军也并未进占租界,又怎么可能毁掉曹聚仁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才收集到的资料呢?思来想去,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应为“一二・八”之误。1941年12月8日清晨,继成功偷袭珍珠港之后不久,日军就借口对英美开战而进占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从而结束了维持四年多的上海“孤岛”时代。这个日子,对当时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上海以及香港等地的人们来说,可谓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也正因此,有时才被一些人称为“一二・八”。经历过现代中国这些劫难的曹聚仁对此当然记忆犹新,因而才会在书中不无感慨地写到:自己寄存于怡和洋行的战史资料,即“毁于‘一二・八’的早晨”。
“一二・八”变成“一・二八”,只是把“・”的位置弄错了,就造成史实上的错误。把“三”整理成了“卅”,更不应该,“五三”怎么成了“五卅”?
该书第一卷引论第39页称:“五卅惨案,为蒋总司令身受最惨痛的打击,当时以坚忍精神克服困难,为后来决志抗战的根本。”这肯定是弄错了。所谓五卅惨案,当指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结果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各界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11人,被捕者、受伤者无数。此事虽然和日本有一定关系,但和蒋介石的对日态度问题好像不太搭界(相反倒引起他的仇英情绪,此后年余其日记里反复出现仇英字样)。真正令蒋“身受最惨痛的打击”并以坚忍精神克服困难,最终成为其决心对日抗战之张本的,应该是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日方称之为“济南事件”)。1928年春,南方的国民党进行二次北伐。在蒋介石的率领和指挥下,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并很快逼近山东。为维持其在华利益,日本想方设法阻止北伐军继续北进。先是借口保侨出兵济南,继而又不顾中方抗议在城内构筑工事。5月3日,日军在济南强行解除北伐军一部7000余人的武装,又以种种借口制造事端,恣意屠杀中国军民。当日深夜又闯入山东交涉使署,杀害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此种暴行随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系列事件,因主要发端于5月3日,故被称为“五三惨案”;又因集中发生在济南,亦称“济南惨案”。此事对蒋介石影响甚大。5月9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然则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不过仅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因此他强调:“余今日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10日,他又在日记中谓:“吾躬逢其惨,不能不为我部属痛耳!”痛定思痛,他亲自定下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后为止”。有关此事对蒋介石对日态度之选择的刺激,在国民党迁台后编定的《革命文献》第19辑中亦有明确的反映。其中收入他1929年5月3日在中央军校的讲话,其题目相当简洁明了,即:《誓雪五三国耻》。只要稍微明了这些史实,当不致如书中出现这样的纰漏。
《采访本记》曾由香港创垦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过。在为三联书店整理出版其作品系列时,曹先生的后人起初只是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本书的目录,而未找到全稿。三联版“采访系列”的外记、二记、三记和新记出版后,台北政治大学的刘维开教授传来消息,说台北某图书馆有此书的藏本。后来又历经一番曲折,内地不少读者才有机会一睹《采访本记》之真容。这本来是件好事。只是因为该书出版较早,又在海外发行,其用语措辞、句读标点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甚至还有些地域特色。惟其如此,在整理时文字校订、标点句读等实非易事(现在整理本的标点情况实难令人满意,有些地方读起来很费劲)。由于客观上存在的时空距离,以及整理者或许不太熟悉相关的历史背景,加之责任编辑可能的疏忽大意,结果现在整理本的个别地方就难免有些处理失误了(按:笔者未见到香港版原书,惟即使确实是原书初版有误,现在整理时也应校订出来)。反过来,这也提醒我们:在整理出版前人文献时,必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而容不得一星半点的马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