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凌晨5点52分,任继愈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任先生已于今晨四时半去世。”我从睡梦中惊醒。尽管我已知道任先生在此前已报病危,尽管我听说任先生因病魔的侵蚀而倍感痛苦,但我仍然不愿相信这一天的来临。又一位自己深深敬重的老先生离开了。我无语,回了一条短信:“深表哀悼!”
第一次听说任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虽学的是中国史专业,但也愿意阅读一些相关相近学科的书籍。在那时,我翻阅了任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说实话,这套书我并没有真正读懂,毛主席对任先生“凤毛麟角”的评价也是以后才知道的。但我觉得这套书的条理很清楚,也因此记住了任先生的名字。
再次听说任先生的名字,是我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华书局工作以后。当时,任先生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负责组织《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纂工作。该项目为任先生在“京西(宾馆)会议”上倡议,得到了时任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列入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指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卷帙浩繁,整理难度大,全书106册(不含索引部分),历时十几年才全部完成。它荣获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该书的编纂,任先生居功至伟。
真正与任先生接触,是我2000年调到古籍小组办公室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岗位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去拜访任先生,请教一些问题,征求一些意见和建议,有时也请任先生参加一些活动。不论是在国家图书馆的办公室,还是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任先生每次都很客气地接待我,很认真地解答我的问题,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不拒绝我邀请他参加的活动。有时,任先生或来信,或打电话,或约我去家里,谈一些与古籍整理出版有关的问题。任先生从不发表宏篇大论,总是用十分平实、简洁的语言,说出一些令人难忘的箴言。在与任先生的交往中,任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睿智,一是通达。在任先生儒雅,甚至有点古板的老派的外表下,总是透出温婉和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任先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同时也很开明。我感觉到,任先生对人对物都很从容。
近十年来,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任先生给我记忆犹新的教诲是:
做好古籍整理,关键不是钱,而是喜好与感情。有钱不一定能做好古籍整理;只要有喜好和感情,没钱也能做好。
出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图书馆的古籍不能只许看(远观)不许摸(借阅)。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并不是善本、古本等稀见版本,而是通行本。
小学教材中,读古诗词早已实行,但“读点古文”(中发[1981]37号文件精神)似乎还做得不够。
重大的项目,没有十来年难以完成。越是重大项目,越需要集体协作。
古籍整理工作既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不计待遇报酬,甘愿奉献的青年人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
领导部门要为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使他们安心工作,生活上足以养家糊口,劳动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他们就会从所从事的专业中得到一些精神安慰。
现在通行的衡量工科、理科的“量化”尺度不适用于选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人才,这一点无可争议。
前一二十年,整理古籍先解决重要而急需的。留下来未能整理的,多属于难度大,不专属于传统经学、史学、文学方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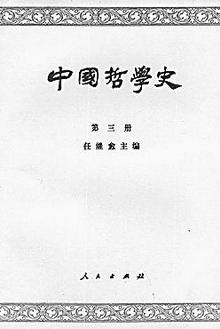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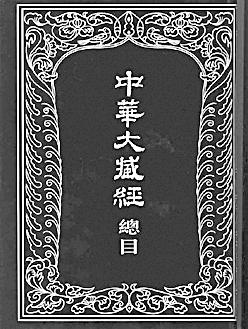 |
现有的古籍整理人才,多能通晓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对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知之甚少。
如果再印“二十四史”,每一个专史附上这个朝代的地图(邻国地形、行政区、边界),就更能体现出现代科学整理的新方法、新成果。《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集体研究的成果,如果有了现成的新成果不用,就跳不出前人窠臼。
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实施,一定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人才比出成果更重要。
如果整理过的古籍,不能准确运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仍然使人看不懂,不解决任何问题,等于没有整理。
古籍整理最难的是今译。注释、校勘不明白的可以跳过去,今译是躲不过去的。
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有待加强。缺了这一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就不全面。这一部分不研究,也难以看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长期共存、互相交融的特色。目前特别需要注意那些已不使用的古文字,如回鹘、西夏、契丹等文字的古籍整理。当务之急,莫过于积累资料(有的已经流散到国外)和培养人才(不贵多而贵精)。现有专家人数少且年事已高,亟待补充新人。培养这类专家,目前采用的培养方式,有些急功近利,在短期内不能要求青年学者写文章,发表文章。应当放眼未来,使青年人打下坚实基础。要求他们通晓两种以上的语言,一种是所研究的语言,一种是汉语,二者缺一不可。更进一步,则要求研究者通晓一种外语,以便及时了解和吸收这些领域国外专家的研究成果。
今人整理古籍要考虑采用新手段。天文志如配以天象图,礼乐志若配以音像光盘、五线乐谱,既省篇幅,又便于读者理解。
古籍整理一概唯古是遵,不敢触动成规,学术就不能前进;前人的成果置之不理,一切从头开始,自以为是新见,反而暴露其孤陋寡闻。两种办法都不可取。
古书中的民族语言、文字,过去只用汉字音译,有时不太准确。如能附上原书的原文,就增加了整理古籍的科学性。
要使当代人在美国电影、日本游戏、韩国连续剧等之外,还能够有兴趣接触一下传统经典,了解一下传统文化的内涵,那么在研究之外,也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普及的整理工作,为普通读者搭建桥梁,不要让他们因为古籍的连属难断、古奥难懂而丧失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普及传播和研究利用并重,将是今后古籍整理的一个方向。
要着手开展综合性整理古籍的工作。所谓综合性的整理,是对同一课题,从不同学科领域、不同角度,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紧密结合,同步进行,协同攻关。
任先生以上的只言片语,看似零散、琐碎、具体,但都是真知灼见,远比那些貌似高远深奥的长篇大论,更加切实有用。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最后一次见到任先生,是今年1月19日。我已离开古籍小组办公室,回中华书局工作。是日上午,我和徐俊同志到任先生办公室向任先生拜年,并汇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工作。任先生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同时也很关心地询问了由中华书局承担出版任务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有关工作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任先生的病情加重了。任先生工作时,是看不出病容的。
4月8日,中华书局聘请任先生为学术顾问之一。当时任先生已住院治疗。国家图书馆为保证任先生安心治疗,劝阻大家不要去探望。4月13日上午,我将聘书和花篮送至李劲同志处,请他下午去医院时转送交任先生。李劲同志后来告诉我,任先生收到后很高兴。
5月底,中华书局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出版合同送交任先生。6月1日,任先生签字认可。任先生的签名仍然一丝不苟。据说,这是任先生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的遗墨。
一个长期研究宗教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醉心于传统典籍的整理工作?任先生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中华秦汉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政府,建国后50到100年间,都是注重文化建设的时期。如汉代从文、景两代到汉武帝约70余年,唐代从贞观到开元盛世、清朝康熙到乾嘉约100年。参照过去,新中国建国到现在50多年了,文化建设也正当集聚资料、准备迎接文化高潮的时期。今天中国正走向世界,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吸收中国的优秀成果,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成果;既要总结古代,又要构建现代。我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资料整理,正是为迎接建设新文化高潮准备粮草。”
我想起了麦克阿瑟1962年5月在西点军校最后的演讲中令世人长久怀想的一句话:“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任先生,走好!
